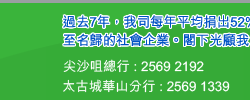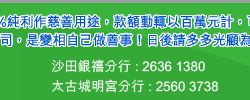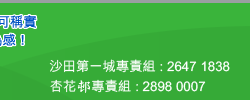小孩子的思想是單純的,他們的心目中人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好人、另一種就是壞人。特別是在“阿香姆媽”(已在“阿香姆媽”一文中敘述了,她和我之間的關係)口中的故事裡更強調的是做個好人,千萬不要做壞人。當然我也不例外,我和其它的小孩一樣往往將身邊的人分成好人或壞人。
1956年我進入了上海市第二女子中學求讀高中。自高中開始我們有三角課程和幾何課程,當時我們的三角和幾何老師是一位大約卅多年歲的男老師。他個子瘦長,他的名字叫趙元濟。由於三角和幾何都是我特別喜愛的課程,當時我們的學習成績是用5分評分制,3分合格、1或2分不合格、4分良、5分優。我的這兩門課不論年中或年終成績始終保持5分,所以趙老師很喜歡我。在上課講解時遇到難題也會經常叫我站起來解答。趙老師永遠是很溫和、有禮地對待每一個學生。即使對學習成績比較差的同學,他總是耐心地解釋、從來不會太凶地責備任何一位同學。所以同學們都特別喜歡趙老師。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學校為學校大掃除,我和趙老師並肩抹玻璃窗。趙老師說我特別聰明,邏輯性強,但是太性急,太呈強也太沒耐心,他覺得我自持學習成績好,所以不夠努力讀書。他囑我努力改正性格中的缺點,並希望我能再努力一些讀書。他相信我一定前途無量。趙老師這番說話我從來沒有忘懷。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非常值得我尊敬並喜愛的老師。對我來說他絕對是個好人。
1958到 1959年間中國大陸掀起反右運動。當年高中學生是不被包括在運動中的,所以我們對運動的具體情況並不瞭解。不過在運動中被劃成右派分子者,都會被認定是因為犯了錯誤,做了對不起國家和黨的事的人。社會上都會和右派分子劃清界線。在我們未成年人的心目中,他們一定是壞人無疑。
有一天,我們的趙老師沒有來上課。代課老師也沒有說明理由。到了那天傍晚,我們班的共青團支部書記,我的好朋友陳文燦偶然聽到教師之間的竊竊私語說趙老師是右派份子,所以晚飯後特地來我家告訴我這一消息。我聽了這消息後心中大驚,但我對陳文燦說趙老師那麼好,我不相信他是壞人,他不可能是壞人。陳文燦同意我的看法,她說她也覺得趙老師不會是壞人。那一晚陳文燦走後我心中七上八下很不踏實,也很為趙老師擔心,我清楚地記得我在日記中寫下了“我不相信趙老師是壞人”。
第二天我和陳文燦倆在課間休息時,到學校教師辦公室周圍去打探消息,我們找不到趙老師的蹤跡。最後在下午放學後,我們在一間學校堆放雜物房緊閉著的門縫裡,張望到趙老師獨坐其中。在雜物堆旁放了一張書桌,裡面有一支很暗的燈。趙老師一手抓筆一手抓了一根香煙坐在桌子前寫東西。我和陳文燦拼住氣看了很長時間,本想敲門進去向他問個究竟,到底他幹了什麼壞事,但我們倆在門口徘徊猶豫了好一會兒,連大氣都沒敢透又怎麼會有膽去敲門,只能懷著沉重的心情離開了學校回家。那天回家後我沒有胃口吃東西,我睡覺前又在日記薄中寫下,“趙老師雖然是右派份子,但我還是不相信他是壞人”。
又隔了一天在上午兩堂課後的大休20分鐘中,我和陳文燦寫了一張紙條從雜物房的門縫裡塞了進去,內容為“趙元濟,(這次我們直呼其名,儘管我倆心中不情願相信他是壞人,但是右派份子一定是做了什麼壞事的人,因此也不敢再稱他為老師)你被評為右派分子,一定是做了壞事,我們希望你徹底自我檢討,交待問題,要相信黨的坦白從寬政策”。
今天回想此事常常會覺得自己當時幼稚無知的可笑。趙老師再也沒有為我們上課。開始時我在學校偶然會遇見他,但他總是低著頭目不斜視地匆匆而過。我雖然非常想和他打招呼,但一想到他是幹了壞事的右派,就每次欲言而止了。在我59年高中畢業前聽說趙老師被調走了,但誰也不敢說,誰也不敢問趙老師去了哪裡。
趙老師的事是我在生命中第一次對好人、壞人概念迷惘不清。現實告訴我右派分子全是壞人,但在我內心深處我始終堅信他是好人。在我幼稚的心靈中,我第一次對成年人對是非黑白的判斷起了懷疑。很多年後我聽說幾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被平反了,我相信趙老師也一定是被平反了,但我一直沒有他的任何消息。今天趙老師如果還健在的話,相信也八十多歲並應該是接近九十歲的人了,如果有任何機會趙老師或趙老師的家人看到這篇文章,我想向趙老師表達的是“趙老師請多保重,其實我一直沒忘掉過你”。
1959年在我進了大學不到三個月時,我們全體師生被召集到學校禮堂,那天在禮堂開了一個反右的聲討會,說是聲討漏網的右派。在臺上跪著一位平頭裝青年,他雖然是低著頭但我相信他只不過20歲左右。臺上站著幾個人訴說那位青年的罪狀,然後帶頭喊口號並吩咐台下的人全部跟著喊。那天的禮堂裡估計有上千人,口號聲可說是驚天動地。在那吼叫聲中我的心第一次真的好像快被震碎了,膽也幾乎給嚇破了。我相信經過那一次,那位在臺上跪著的青年,非但一輩子不會再得安寧,而且非得夜夜在惡夢中驚醒。
我當時才18歲,在我的成長環境中幾乎沒有暴力,我在戲劇電影中雖見過殘酷的戰爭場面,但是我從來沒有身處其境的感覺。我也第一次感到在人類斯文的外表下,人的內心是蘊藏著粗暴和殘忍的。因為我對學校的一切都還十分陌生,所以也不知道那位青年人是誰,對他的下場當然也不知道了。但我心底裡一直對他有一份同情。
在大學時我讀的是物理系,但數學一直是必修課。我的數學教授的助教是一位由北京大學數學系畢業的年輕人。他和我們的老教授同為北京大學的右派分子,所以一起被調來安徽大學。當時的安徽生活條件和北京、上海和其它大城市差距很大,所以很多非右派的教師不肯來安徽任教。但因為右派分子沒有多大的選擇,所以我們學校就有特別多右派教授和助教。其實當時被劃成右派的幾乎都是在學術上很有成就的專家,所以我們安徽大學雖然非第一流大學,但師資力量卻並不弱。我們那位助教年齡最多比我大十歲八歲,他的名字我已記不清楚,但我對他那對充滿憂傷的大眼睛裡的眼神卻記憶猶新。他沉默寡言很少和學生溝通交談,他也不大有笑容,而且總是獨來獨往。但他很斯文,對任何人都很和善。我和他也沒有太多的接觸,但我挺喜歡他衣衫整潔、彬彬有禮的外表,我也特別想知道他那眼神為什麼總是充滿憂傷,當然我從來也沒問過他這個問題。我不知道他是究竟為什麼被劃成右派,聽說是因為他會拉小提琴,而小提琴的曲子幾乎全都來自西方國家,在當時崇洋聽西方古典音樂都會被認為是思想上的腐化和墮落。當然這是不是他被劃成右派的真正原因我無從得知,也不敢問他。但是有一次我去他宿舍將同學們在自修課後的作業簿交給他的時候,他開門從我手中接過作業簿那一刻,我能聽到他房間裡的收音機正播放著俞麗娜的“梁祝協奏曲”,我也仿佛見到他那對大眼睛裡隱約地泛著淚水。在那一刻我對他除了同情外,更多的是惋惜和憐憫。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已忘掉他的名字,但我直到今天都不能忘卻他那對泛著淚水且充滿憂傷的眼神。
“右派分子”對很多年輕人來說是一個非常陌生,且不容易聽明白的名詞。在我的生命中有幾位老師和一位堂姐夫是右派。我的堂姐為了她的丈夫是右派而受盡苦難,她的孩子們也在社會上受盡白眼,我和這位堂姐夫從來沒有什麼接觸,但我知道他不是壞人。而我的老師們在我的心目中,就一定不是壞人。即使他們在社會上已被公認為壞分子後,我的直覺還是告訴我他們是好人。歷史也證實我的直覺沒有錯。他們現在已經都被平反了。不過相信這些被劃成右派分子的人,雖然名譽被恢復了,但他們精神上的損失,和他們心靈上曾遭受的痛苦是永遠無法彌補的。令我慶倖的是,雖然我們曾為這些發生過的事情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它們都已成過去,相信類似的事情是永遠不會在我們的生活中重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