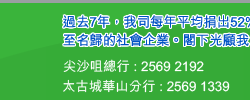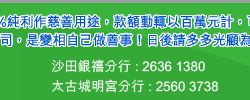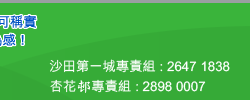很多人問我,為什麼畢業退伍之後會選擇這個不起眼的小醫院作為自己醫師生涯的起點,這個問題連我媽都問了我好幾百次。同學們畢了業大多是留在醫學中心或大型教學醫院,按部就班的過著一年捱過一年的住院醫師生涯,很少有人會像我們這群傻子一樣,窩在這種工業區裡的小公家醫院一待就是好幾年。
醫學系的最後一年來到這家醫院實習的那兩週之前,我根本聽都沒聽過這家醫院,來實習的第一天早上還是看著地圖找到的。急診外科的醫師恰巧是以前醫學院棒球隊熟識的學長,我那時候實習的工作就是協助學長作一些簡單的縫合。
那天早上,一個長得像外勞的先生握著自己的手臂衝進急診室,鮮血染紅了他沾滿污漬的工作服。拉開他的袖子之後我當場楞在那兒,他的整隻前臂的皮膚都像龜殼一般裂成碎片,可是底下的肌肉血管卻好端端的在那裡搏動。隨後趕來的工廠領班說,他是被一台真空吸引的機器把整隻手臂吸進去,經過簡單的檢查我們也發現他的手部功能大致完好,就是真的「體無完膚」,整隻前臂的皮膚就這樣爆裂成小指甲大小的碎片。
當然,這種單純的縫合就是我的工作。
準備好縫合需要的器械,我開始很專心的修補起那隻支離破碎的手臂。這種縫合對當時的我來說已經是足以勝任,只是他受傷的範圍實在太大,所以需要一些時間讓我慢慢完成。那位外勞也很配合,從打局部麻醉到縫合沒哼過半聲。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我一針一針細細的縫也縫了快兩個小時。那工廠的領班忽然闖進急救室來,有點不耐煩的問我:「醫生啊,還要多久?」
「大概再半小時吧,快好了。」我頭也沒抬的說:「唉呦……醫生啊,那個外勞隨便縫一縫就好啦,我還要帶他回去耶。」
我放下手中的器械,抬起頭白了那個工廠領班一眼,沒好氣的回他一句:「如果你是外勞,你要不要讓我隨便縫縫就好?」他聽了閉上嘴,識相的關上急救室的門出去,剩下我和那外勞,還有一室的死寂。
「謝謝你,醫生……。」幾分鐘之後,那外勞忽然用還算標準的華語對我說。
這下子換我呆在那裡,不曉得該說什麼。
「你會說中文?」心想他整整兩個小時沒出半點聲音,害我以為他聽不懂也不會說中文。
「我是泰國華人,從小就說中文的……謝謝你喔,醫生。」
接下來的半個小時,我和他聊著他來台灣當外勞的點點滴滴,是如何在泰國泡沫經濟破滅之後離鄉背井,在台灣孤家寡人一個是怎麼樣被工廠的老闆壓榨,被工廠的領班欺負,又是如何的思念著千里外的妻兒。
那天,台灣股市再度站上萬點,可是自小在都市長大的我,第一次清楚而深刻的的感受到台灣的經濟奇蹟不是振臂高呼「福氣啦」,也不是經濟學課堂上的GNP與M1b,更不是宣導短片裡熙來攘往的人群與林立高聳的摩天大樓,而是每天每刻,被送來急診的這些殘臂斷指血肉點滴的累積。
畢業退伍之後,我就這樣放棄了原本可以留在中山南路那座醫學聖殿的機會,來到了這個工業區裡髒髒暗暗的小公家醫院。不為什麼,只是因為對我而言,醫學不只是穿著白色的醫師服躲在象牙塔裡供人景仰,或是淹沒在生化科技的迷思之中。既然醫學是「Science of Life」,失去對生命脈動的感受,離開人與人生必須經歷的苦難、折磨、矛盾、掙扎與無奈,醫學就只不過是利用著玩弄人性對關懷的需求及死亡的恐懼作為手段的高科技生化服務業而已。在這裡每天看到的病人大多是社會最基底的一層,感受到屬於臺灣社會的生命脈動也更真實而強烈。
有次在急診一位中年婦人握著自己受傷的手平靜的走進來,污黑的棉布手套滲著血漬,應該是指頭的地方早已經被碾壓得扭曲變形,皮膚和肌肉的碎屑夾著棉布的纖維,就這樣硬生生的從棉布手套的隙縫中被擠壓了出來。小心翼翼的幫她脫下棉布手套,右手食指和中指已經變成一堆滲著污血的碎肉渣,沒有什麼重建的希望,只有截肢一途。
我請那為婦人先躺在床上,先幫她做傷口的沖洗及初步的包紮,準備聯絡開刀房進行受傷手指的截肢。這樣因為工作職業傷害的病患每天都有好幾個,大部份的病患都會因為情緒的激動加上傷口的疼痛而哀叫或哭泣,可是這位婦人卻出乎意料的冷靜與平靜。
「傷口會不會很痛?需不需要我先幫妳打一支止痛針?」我擔心她是不是快痛暈了所以才不說話,可是婦人平依舊平靜的搖搖頭。
「妳這個是被『普列斯』〈press,沖床,一般都直接台語音譯稱呼〉壓到的吧?」看著她的傷勢,這樣的傷一早上已經是第四個,一面包紮我一面問著。
「這隻手已經被機器壓過三次了,」婦人看著自己即將被截去的手指,不帶任何情緒的淡淡的說著,好像受傷的不是自己的右手一般,「前兩次運氣好閃得快,只是皮肉傷,這一次終於還是閃不掉……。」
我抬起頭望著那位年齡和自己母親相彷的婦人,心裡瞬時被潮擁而至的心痛與不捨所淹沒。
「……這一次終於還是閃不掉……」要多少的苦難和艱辛,多少的血淚和痛楚,才能把一個靈魂折磨得只剩下對生命的妥協與對命運的無奈?
「妳前幾次受傷之後,難道工廠都不會想辦法改進那些機器的操作方式嗎?」那年還天真稚嫩的我這麼無知的問著。
婦人輕輕的嘆了一口氣,不像在難過自己即將失去兩隻手指,倒像是在喟嘆我對世事的無知,「有工作做就已經很偷笑了,老闆連發薪水都快要發不出來了,哪還可以改什麼機器操作的安全?……再說為了家庭和孩子,再怎麼明知危險也不得不做下去啊……有工作做還算好的咧,我們左右旁邊的其他工廠,老闆都說過完年要等通知再來上班……」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或能夠說什麼。手外科的教科書上在第一章的第一段就開宗明義的告誡我們:"Each inch of one's hand equals to each inch of one's financial life",可是教科書上不會告訴我們,當這些失去的手指或臂膀代表的是生活的重擔,雇主的壓榨,未來的茫然與不知所措,或是許多生命中不得不面對的無奈時,我可以為這些已經失去的做些什麼。對醫師而言,這樣的一位病患不過是每天眾多職業災害的受難者之一,可能只是開刀房白板或護理站櫃檯上的一個名字。對雇主或政府而言,這樣的一位病患可能只是職業傷害通報的一個數字,或許只是勞工保險幾萬塊錢的補助和一紙殘障證明。可是對病患而言,失去的可能是一輩子的工作能力和一個家庭的經濟支柱,這些都不是任何的手術或津貼可以修補或補償的。
每天每天,看著一個又一個職業傷害的受難者以數不盡的殘臂斷指堆疊著台灣經濟架構的最底層,也不只一次聽見病人苦笑著告訴我「沒法度啊……遇到了就要認命,艱苦人生成就是這樣」,自己真的不知道該為這些人的遭遇喟嘆,還是為台灣人對生命無奈的妥協及不得不的樂觀與韌性覺得悲哀。
不久之後,一位攝影家恰巧舉行關於職業災害的攝影展,我特地去仔細參觀了一下。黑白的巨幅相片聳動的對比著一幅又一幅的傷疤特寫。當天去參觀的人不多,我靜靜的在偌大的展覽室裡看著聚光燈下那一張張傷口瘉合多年之後的影像,可是腦海中浮現的卻是這樣的傷疤在受傷的當時會是如何的血肉糢糊,傷者會是如何的握著自己的傷肢一路滴著鮮血哀嚎著被送進急診,又在那一切的傷痛與憤慨都成為過去之後必須學會無奈的樂觀與接受,卻還是可能為了生活的現實又必須讓自己殘存的軀體繼續埋葬在經濟奇蹟的榮景之下,再一次的被踐踏著屬於台灣人的堅強與韌性……。
知道自己並不能為這些人多做什麼,明天一早上班依舊會有這樣的殘臂斷指被送進急診來,屬於這個社會的傷痛,無奈與承擔一樣會不斷的在這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反覆繼續。可是當我走進我們每日住院費只要99元的健保病房,看見那一位又一位手指或手臂的殘肢上纏繞著紗布的病患,依然彼此談笑著,互相鼓勵著,關心著彼此的傷勢;嘲弄著,戲謔著彼此生命中的無奈。我知道他們必須學會如此,才能讓自己苦笑著活下去。只好每天看著左手受傷的,慶幸自己不必像鄰床右手壓碎的必須學著用左手吃飯寫字;右手受傷的說,他比隔壁房那個鷹架摔下來下半身完全癱瘓的要好得多了;可是那位從高樓鷹架摔下,肝臟脾臟破裂,腹腔大量內出血,胸椎粉碎性骨折,脊髓嚴重損傷及雙下肢癱瘓,歷經生死關頭從鬼門關被救回來的那位病人卻說:「能夠活著就好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