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
神童,顾名思义,神一样的儿童,是对天赋异禀儿童的一种称呼。
作为一名业余的“码字人”,探花郎也知道几个古代神童,蔡伯俙3岁中进士、孔融4岁让梨、晏殊5岁咏松、曹冲6岁称象、骆宾王7岁咏鹅、甘罗12岁当丞相等等。
当然还有更厉害的,葫芦娃一出生就会打妖怪。
本文主人公司马光,小时候也被人称作“神童”,他7岁咏缸,哦,不,是砸缸。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我们从小听到大,都要听吐了,让你再听一次,那就是折磨你了。
司马光一砸成名,成为了家长眼中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成年后的司马光,但凡与生人交往,他一报姓名,对方立马惊呼:是砸缸救友的司马光吗?
待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又是一通狂赞:啊,君实真是机智啊,当时你是怎么想的?缸砸坏了怎么向父母交待?那么重的石头你搬得动吗?-----
司马光一脸苦笑:砸缸救友,乃情急之下的生理反应自然反应,没考虑那么多。
那么问题来了,当有人坠缸时,为什么其他的小朋友都一哄而散,唯独7岁的司马光会砸缸,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②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司马光出生在河南光山县县衙官舍。因出生在光山县,光山县县令、父亲司马池给他取名司马光,字君实。
司马池进士出身,博学多才,官居天章阁待制(四品),性质朴平和,为官清正廉明、不阿权贵。为子死孝,为了回家探望发病的母亲,他毅然放弃殿试资格、放弃将要到手的进士。
没有谁可以随随便便成功。司马光7岁砸缸绝不是偶然的,靠的是平时的点滴积累,包括他后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方面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和父亲司马池的言传身教也是分不开的。
司马光6岁时,父亲就开始教他识字读书。《宋史》中记载:“光生七岁,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司马池除了教授司马光文化知识,更注重对他思想品质的培养。
司马光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姐姐帮他脱青核桃皮,没脱成,离开了,一个丫鬟用开水烫,成功脱皮,姐姐回来问他是谁脱的皮,他说是自己。
此事恰好被父亲撞见,父严厉呵斥:“小子何得谩语!”司马光从此不敢再说一句假话。为此,司马光特地把这事写成条幅,时刻警示自己。
我们知道,宋代地方官实行任期制,一般二到三年为一任,官员转任调动频繁。父亲司马池作为一名地方官,自然也要到多个地方做官。
司马光在少年时期,就跟着做官的父亲四处游学,耳濡目染,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生活阅历和社会知识。
父亲司马池办公、接待官员时,司马光就在旁边观察“实习”,可以说从小就开始学做官了。什么样的家庭出什么样的孩子,这句话有它一定的道理。坊间俚语不是也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③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20岁的司马光参加进士科考试,一举而中,中进士甲科第六名,继砸缸之后再次名动京师。之后不久,以奉礼郎出任华州判官,赴任前又喜娶财政部副部长张存的三女儿张氏为妻。
金榜题名、官袍加身,洞房花烛、佳人相伴。年少成名的司马光,人生开局堪称完美。
只是老鸡汤又说,没有谁的人生可以完美无缺。司马光也不例外,先是母亲去世,他不得不中止仕途丁忧,接着为官正直的父亲又遭小人陷害,被贬官,不久也抑郁而终。
没有了父母的遮荫庇护,司马光不得不独自直面人生风雨。
“执丧累年,毁瘠如礼”。1044年,为双亲守孝四年期满后,司马光被任命为滑州判官,不久进京升为大理评事兼国子监直讲。
刚复出不久就升为京官,年轻的司马光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在和滑州同僚告别时,司马光写下了《留别东郡诸僚友》:
际日浮空涨海流,虫沙龙蜃各优游。
津涯浩荡虽难测,不见惊澜曾覆舟。
我们知道,司马光一生从政四十余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机关工作,基层工作经历了了,不像跟他一生相爱相杀的王安石那般,有着20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且政绩显赫。
司马光偏重理论,遵道守礼,教条死板,王安石则灵动机变,思维超前,头脑中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司马光父亲司马池是一个“不胜繁剧”的人,司马光也很像父亲,并非是个能员干吏,说白了就是不喜欢“俗务”,喜欢讲礼研道、做学问,属学术型人才。
1048年,司马光在参知政事、恩师庞籍的推荐下参加学士院召试,顺利通过,被任命为馆阁校勘。
馆阁社会地位高、发展前途大,属“清要之臣”。在馆阁任职,既可读到外面读不到的书籍和档案,还可以经常和皇帝面对面交流。贴近领导的好处大家都懂,贴得越紧机会越多,宋代两府大臣多是馆职出身。
进入馆阁任职,对喜欢读书做学问的司马光来说,真的是把兴趣爱好和工作完美结合起来,算是人岗相宜吧。那么,在馆阁任职的司马光,就真的甘于“寂寞”、专心做学问吗?
④
提到司马光,给大多数人的印象除了会砸缸外,就是一个老顽固、老古董,是封建礼教的守护人,是一个愚不可及的“迂叟”。其实年轻时期的司马光,也是一腔热血、怼天怼地怼空气的“直男”一枚。

接上文,进入馆阁任职的司马光,算是刚入职的新人,按照我们现代的职场规则,新人应该先熟悉工作环境,跟领导套套近乎,了解领导脾性,以便相机而动。
然而,司马光不讲武德,刚上班就对顶头上司孙抃发难。原来,司马光在翻阅日历时,发现本朝的两件大事没有记录。一件是元昊称帝,一件是割南地于辽。
作为未来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司马光要求将这两件事补上,而孙抃以“国恶不书”为名而拒绝。
但司马光不依不饶,“教育”顶头上司孙抃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一定要补记这两条,不记上我就报告老板-----
搞得孙抃心里mmp:哪来的生瓜蛋子,你还是回家砸缸吧。
不久司马光就因“工作需要”调任同知太常礼院。谁知,司马光秉性不改,到了太常院屁股还没坐热,又连开三炮,两炮打皇帝,一炮打恩师的恩师。
大宦官麦允言死了。仁宗念其在身边服侍日久,就破格给他封了高官、高规格举办葬礼。
仁宗的决定有悖于礼,但既然皇帝发话了,朝臣大多装聋作哑,不就是赠个官、葬礼规格有点高嘛,何必为此得罪皇帝。
但司马光不干了,一个死宦官凭什么享此哀荣,这是违反礼制的,只有为国立过大功的人才可以享受。司马光给仁宗摆事实、讲故事,务必要仁宗收回成命。(仁宗到底收没收回成命,史书未见记载。)
仁宗厚宠四川美女张贵妃,结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贵妃伯父张尧佐,从一个小州知州越级提拔为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这还不算,不久又加封其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一身兼五使。
仁宗这事做得有点过分了呀。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是黑脸包公包青天包拯包大人。
他近御前据理力争,情绪激昂唾沫星四溅。包黑早饭吃的可能是韭菜盒子,只闻一股呕心的味道,掺杂着口水喷向了仁宗,仁宗尬尴至极,身体连连后倾“以绢拭面”。
“入戏”太深的包黑却浑然无视,对着仁宗仍旧是滔滔不绝,一刻不休-----
吃了囗水的仁宗皇帝不生气不妥协不退让,接连外放了几个谏官,包黑“力竭”,无奈止步,朝堂一片寂静。
司马光一看,哟嗬,连老包都怂了,看我的。司马光连夜上书《论张尧佐除宣徽使状》说,最近开封连日雾霾加冻雨,这是天子不虚心纳谏造成的。
接着他又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说有个老农特别爱惜自己的瓜秧,在太阳当头的时候也去浇水,结果把瓜秧浇蔫了,这是好心办坏事。陛下加爱张尧佐,是人之常情,但越级提拔,拒绝纳谏,也是好心办错事呀。
司马光一会搬出老天吓仁宗,一会又给仁宗讲故事,软硬兼施。仁宗一听,有道理,最后作出让步,除去张尧佐宣徽南院使等职务,并让其离开京城到外地任职。
最后一炮打夏竦。夏竦是仁宗的老师,仁宗对他宠爱有加,但夏竦是个有才无德之人。夏竦曾经救过司马光恩师庞籍的命,庞籍的升迁也与夏竦的大力推荐有关,算是庞籍的恩人。
夏竦生前爵为英国公,职为宰相兼节度使,是朝廷一品大员,死后按规定要给谥号。仁宗念旧,直接决定给夏竦谥“文正”。
这下子朝廷炸了锅。按《谥法》,“文正”可是最高一等,夏竦有才无德,奸邪好色,不配这个谥号。
司马光立即率礼院同僚上《论夏竦谥状》,一面指出仁宗给夏竦谥号没有送太常院议谥、经中书省审定,程序不合法;一面列举夏竦劣迹,称其不配“文正”谥号。
(Yy司马光:夏竦你不配,文正是留给我的,哼!)
夏竦劣迹仁宗门清,众怒难犯,仁宗最后无奈改夏竦谥号为“文庄”。
⑤
人在官场飘,哪能不挨刀。1053年七月,司马光恩师庞籍遭人陷害被罢相,贬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县)兼京东西路安抚使,离京前,他点名要司马光为通判。
司马光在京城风头正劲,庞籍为什么要司马光跟他一起“贬”?
原因有二,一是司马光在论张尧佐和夏竦时,已卷进政治漩涡,早晚会被人“惦记”,庞籍这是间接保护他;二是司马光州县工作不足,宰相起于州县,如果不补上这一课,对他发展前途有影响。
所以说,姜还是老的辣。只是此时司马光未必能明白恩师的良苦用心,但司马光是一个感恩的人,庞籍有恩于他,他二话不说,跟着庞籍就去了郓州。在郓州,庞籍有意栽培司马光,将郓州州务全部交给他处理。
面对繁杂琐碎的州务,司马光左支右绌、相当狼狈,这才知自己才疏学浅,吏治非自己强项,“诚知才智微,吏治非所长。”
庞籍文武全才,在西北与韩琦、范仲淹齐名。并州(太原)北与辽、西于夏对峙,急需一大员坐镇,庞籍又被调到并州主管军、政,司马光继续追随恩师,改任并州通判。
并州是宋的北部边城,苦寒之地。司马光的两个幼子水土不服相继夭折。痛失爱子,司马光夫妇悲痛欲绝。也许是过度悲痛引起内分泌紊乱,司马光妻子张氏再也没能怀上孩子。
丧子之痛伴随着司马光一生,二十年后,司马光梦见稚子,写下令人心酸动容的《梦稚子》:
穷泉纤骨已成尘,幽草闲花二十春。
昔日相逢犹是梦,今宵梦里更非真。
“三千之罪,无后为急。”张氏觉得对不住司马光,先后派出两名美女对司马光实施“美人计”,奈何司马光天生不喜欢新事物,美女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拿下司马光,只能悻悻而归。
张氏企图让司马光纳妾计划失败,最后只好过继司马光侄子司马康为养子。
不近女色的好男人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古今皆然。那么生活中的司马光应该是一个很无趣的人吧,其实不然,司马光也一个段子手。
某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张氏兴冲冲对司马光说:君实,晚上我们出去看灯吧?
司马光:看灯?家里不是有灯吗?
张氏:不光看灯,还看人。
司马光:看人?难道我是鬼吗?
张氏:emmm-----
看看,什么叫把天聊死,这就是。
当然,司马光此事硬“杠”张氏,其实他是在生闷气 。我们知道司马光是一个极度节俭的人,俗话叫“抠门”,他早就对上元之举国观灯的风气看不惯了:满大街亮那么多灯,这要花国家多少钱呀!
看似老古董、不懂情调的司马光,你别以为他只会搞研究、做学问,他写起艳词来,那也是别有一番风味,正如后人所说“此公风情亦不薄。”
司马光一生专注经史,对旁门左道的小词自然看不上,留下来的词不多,大概只有三首,欣赏一下他的《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多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
当然,在高官纳妾成风的宋代,身居高位而拒不纳妾的不只司马光一人,他的老朋友老对手王安石同样不近女色、拒绝纳妾。这和如今的一些贪官相比,啊,我呸,贪官就是一坨臭狗屎,谁和他们比。
并州处在抗击辽夏第一线,军务繁重。司马光初次接触军队,外行看热闹,他显得比较兴奋,挥笔写下了《塞上四首•其一》:
未得西羌灭,终为大汉羞。
惭非班定远,弃笔取封侯。
司马光渴望能像汉代班超那样投笔从戎、建功立业。他建议在麟州屈野河西岸筑堡寨以抗击西夏,只是司马光缺乏军事斗争经验,也没有深入屈野河前线侦察,结果宋军在屈野河遭到伏击,损失惨重。
对此,朝廷派侍御史前来查处屈野河案。此时司马光已接到调令,回朝任祠部员外郎。
在御史到来之前,庞籍催司马光快走:“此事与你无关,我是统帅,一切由我承担。”
司马光生平第一次违抗恩师,坚决不走:“责任在我,我一定要跟御史说清楚。”无论庞籍怎么劝,司马光就是不听,非要等御史来了说明真相,要承担首要责任。
而屈野河案的处理结果有点出人意料,庞籍被削去节度使,改知青州,相关责任人都受到了免职、降职和开除等处分,唯独司马光非但没被处分,还相继升为开封府推官、判三司度支勾院,这又是为什么呢?
⑥
在屈野河案中,责任人司马光非但没有受处分反而升官,在外人看来他有卖友求荣嫌疑,为此司马光也是一头雾水、郁闷不已,他一再拒绝升职,一看见人就拉着人家,像祥林嫂一样反复絮叨:我真傻,真的-----
事出反常,必有原因。原来早在四年前的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在逝世前向仁宗推荐宰辅之才,司马光名列其中,仁宗没有忘记范仲淹的遗言,早把司马光当作后备宰辅培养呢。
就在司马光还在为自己升官闷闷不乐时,一个人的到来,像一束阳光驱散他心中的雾霾,这人正是日后他最大的政敌王安石。
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只因试卷中一句“孺子其朋”惹脑仁宗,到手的状元飞了。
王安石长期在州县任职,政绩显赫。因屡屡拒绝京城美官,让他名声大噪,是当时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此番进京到三司使任职,算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吧。
同在三司使任职的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和王安石,人称“嘉佑四友”,只不过后来“嘉佑四友”中有三人都成了王安石政敌。
司马光久闻王安石大名,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很快成为至交。王安石不修边幅、身上虱子多得也像的声名一样,天下皆知。
一天,苏洵和司马光聊天,苏洵说王安石“囚首丧面”,还说这种人一旦得志会乱天下的,问司马光怎么会和这种人交朋友?司马光听了,一脸茫然。
有一次,王安石和朋友们围炉夜话,谈笑间,王安石就从身上摸出几只虱子,随手扔到炉火里“啪啪”作响,就像炸鞭炮一样。
后来王安石还写过一首《烘虱》诗,“未能汤沐取一空,且以火攻令少挫。”水淹不行,那就火攻,务必要将虱子们一网打尽。
司马光看到后,专门写了《和王介甫烘虱》对他进行调侃批评,“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你看看,两个大学士先跟虱子干上了。
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轮流带着王安石到定力院洗浴,把他的脏衣服收去浣洗,再给他准备好一套新衣服,王安石见到新衣就穿,也不问哪来的,此事史称“拆洗王介甫”。
那么同在三司使上班的司马光和王安石,这对老朋友、老冤家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⑦
1060年底,司马光和王安石同时接到新的任命:同修起居注。起居注是负责记录朝廷日志的秘书,包括记录皇帝的言行,任期满后可升为知制诰、翰林学士,然后便可进入执政行列。
可出人意料的是,面对这个人人求之不得职务,司马光和王安石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请辞。当然他们也不是假客气,王安石8次上书请辞,甚至为了不接受任职书竟然躲到厕所里。
司马光呢,也连上三道辞呈,后来听说王安石都上了8次辞呈了,马上又上了第四、第五状,在第四状中把王安石当参照物,说王安石文辞闳富当世罕见,自己的才能不及王安石之一二,王安石的水平那么高,尚且不敢接受,何况我呢?
只是仁宗御笔轻轻批了四个字:不许辞免。他们只好乖乖地上班去了。
1061年,就在他们被“逼”着当了修起居注不久,王安石被提拔为知制诰,司马光被提拔为知谏院。有意思的是,这次他们俩又好像是约好似的,竟然没有请辞,欣然上任。
顺便说一下,后来神宗即位,任命司马光为斡林学士,司马光真的不想干,就接连上了二道辞呈,神宗还以为司马光是谦虚假客气呢,就没搭理他。
司马光见神宗没回复自己,就上了第三道辞呈,于是宋神宗就传他上殿。
宋神宗:“司马爱卿为何不接受翰林学士?”
司马光:“回陛下,臣不能为四六。”
宋神宗:“不能为四六?卿能高中进士第六名,怎么就不能为四六了?”
司马光一时无言以对,扭头开溜。
宋神宗笑了,派宦官追到门口,强迫他接受告敕,司马光却拜而不受。
宋神宗见状:“司马光还不回来谢恩!”司马光不得不回来,还是拜而不受。
神宗命令宦官:“塞到他怀里去。”
翰林学士可是多少文人士大夫的终极梦想呀,司马光却待之若此,只能说司马光既有才又有个性吧。
仁宗后期,北宋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有识之士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司马光、王安石分别给仁宗上书《进五规状》和《上时政疏》,为大宋的长治久安建言献策。
但二人的建议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司马光是对照儒家仁、孝、礼、乐来找差距,“谨遵祖宗之成法”;王安石则透过现象看本质,一针见血:大明法度,众建贤才。
他们都看到了朝廷弊端,有共同语言,但在治国思路上,二人可以说是水陆不同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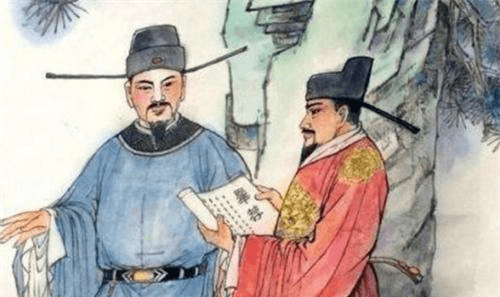
虽然治国思路不同,但此时二人尚未进入执政,没有话语权,既使他们说得再多,也只能算是“口嗨”,所以他们之间还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后世把仁宗说成是宋朝最好的皇帝,但只是好在“仁”字,其实他是一个贪图安乐、不思进取的皇帝。
司马光、王安石纵有滔天的治国方略,仁宗也不会采用,他是一个怕事、得过且过的皇帝,“庆历新政”昙花一现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
关键是,仁宗皇帝现在忙着生儿子,哪有心思听你们瞎啰嗦。
⑧
仁宗的父亲宋真宗赵恒有六个儿子,但活到成年的就仁宗这一棵独苗,而到了他这里,现在都50多岁了,愣是生不出儿子。
当然,也不是仁宗有什么夫科病不能生,只能说他命不好吧。他成群的后妃一共为他生了13个女儿(9个早夭),三个儿子,一个没活。
皇帝不急太监急。大臣们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仁宗生出儿子,于是频频上书:皇帝呀,先从宗室中过继个侄子过来,充当储君吧,国家社稷重于泰山呀。儿子你慢慢生,我们慢慢等,到时等你生出儿子了再调换。
每每碰到这种情况,仁宗总是笑眯眯地说:不急不急,后宫有人怀孕,不久就将生产。潜台词是,我要让自己的儿子来接班。
君无戏言,仁宗的确没说谎,两年来,后宫有五个嫔妃先后怀孕,可生出来一看,全是小瓦片小棉袄,就是没有一个带把的,仁宗急得眼都绿了,空欢喜五场。
而这时又传来一个坏消息,仁宗中风了。以韩琦为首的群臣更急了,立储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平稳过渡,万一哪天仁宗突然崩了,谁来继承皇位?到时还不知会发生什么大乱呢。
在韩琦的授意下,群臣纷纷冒死上书立储,但都被仁宗给拒绝了。立储虽说是国事,但也是皇帝的家事,过份操心,恐怕会招来杀身之祸。
就在韩琦一筹莫展时,史学家司马光站了出来,他剑走偏锋,仁宗召见时,他直截了当地说:陛下对立储一事犹豫不决,一定是受了小人的迷惑,说什么陛下春秋鼎盛,子孙当有千亿,何必急着做这种不祥的事。
其实他们并不是为江山社稷着想,而是想着到时候拥立他自己的人。
仁宗:拥立自己的人?谁?有这么严重吗?这一下子就戳到仁宗痛处了,当皇帝的最害怕皇权旁落了。
司马光手持笏板,向前一步:陛下,您看,唐朝自文宗之后,皇帝都是近臣拥立,“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事您一定听说过吧?大宦官杨复恭操控太子废立,这才是国家不幸呀,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呀。
仁宗脸色煞白,沉默不语,此刻空气似乎都要凝固了,良久,他发话了:司马爱卿所言极是,朕决定了,立宗室赵宗实为皇子,只要皇帝姓赵就行。赵宗实就是后来的宋英宗赵曙。
就这样,司马光凭着过人的智慧和胆识,让悬而不决的立储问题尘埃落地。凭此功劳,经仁宗批准,任命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赐三品服。此时司马光年仅44岁。
因此事,后来欧阳修在离开朝廷前,向神宗推荐司马光时还评价他:“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
⑨
曾几何时,大家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新闻,某某人办某某事,当事人被要求提供“你爸是你爸”的证明,身份证和出生证都不好使的那种,当时在网上引发极大的争议。
而在北宋,也发生了一件让我们现代人觉得很奇葩的事——濮议。那么什么是濮议呢?所谓濮议,就是关于英宗的生父赵允让该怎么称呼的问题。
上文说过,仁宗无子,便立堂兄濮王之子赵宗实为皇子,改名赵曙,继承皇位。
赵曙当了皇帝后,要追尊生父,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生父就是生父,叫父亲天经地义,这本来就不是个问题,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也是持这种观点。
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台谏不干了,说赵曙是过继给仁宗后才继承皇位的,既然称仁宗为父皇了,赵曙只能称亲生父亲为皇伯,这就是所谓的“尊无二上”。
当事人英宗皇帝被气得要脱龙袍不干了,怎么当个皇帝还把父亲当成伯伯了?
两派为此争得不可开交,难分伯仲,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台谏人数占优,司马光上书英宗,要求英宗采纳大多数人的意见。
英宗心中不快,对司马光的上书不置可否,兹事体大,以拖待变吧,濮议一事被无限期推迟。
就在濮议之争如火如荼时,司马光升官了——龙图阁直学士,不再知谏院。这事是不是有点玄妙?好,接着看。
那么濮议之争最后的结果如何呢?
英宗最后支持采用欧阳修的“降而不绝”论,这也是可预见的结果,英宗终于可以把爸爸叫爸爸了。
台谏对英宗的决定表示不服,纷纷以辞职相威胁,英宗也一一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将吕诲、范纯仁(范仲淹子)、吕大防等台谏成员外放,而之前领头的司马光却毫发无损,还升官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Ps:在四百多年后的明朝,也发生一件类似的事情,叫“大礼仪”。
明世宗朱厚熜,也就是嘉靖帝,他以皇侄身份继成大统,也被要求换爸——把亲爸叫叔把亲叔叫爸。
嘉靖帝当然不干:父母也是可以随便更换的吗?!
左顺门外二百多位群臣,看上去黑压压乌泱泱的一大片,跪伏哭谏——坚决要让嘉靖帝换爸。
年轻的嘉靖帝继承了老祖宗朱元璋的狠辣一面,“社会我朱哥,人狠话不多”,直接下令锦衣卫廷杖伺候。
一时间,左顺门外大棒横飞噼里啪啦此起彼伏,“万户捣衣声”,被摁在长条凳上的群臣被捶得死去活来哭爹喊娘,翰林院编修王相等17人当场被活活打死,没被打死的,停薪的停薪,发配的发配,退休的退休。
“大礼仪”之争以嘉靖帝的完胜而告终。)
⑩
在濮议之争中,欧阳修的“降而不绝”论胜出,司马光的“尊无二上”论落败,台谏不服,被英宗外放殆尽,领头的司马光因升官“幸免”。
当然不存在所谓的幸免,这不过是首相韩琦的提早布局,他对司马光是爱护的,而爱护是为了更好地利用。韩琦老谋深算,直肠的司马光老是被他利用。
英宗当皇子的时间短,没有接受太子应接受的系统教育,司马光史学功底深厚,正是帝师的合适人选,这是韩琦早就谋划好的。司马光在给英宗授课的过程中,私编了《通志》8卷作为教材。
也是在这时候,司马光萌发了编一部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止共16朝1362年的史书,供帝王“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只是工程量浩大,仅凭司马光一人无法完成,司马光向英宗请求支援,英宗完全同意。
之后不久,在英宗的支持下,编修书局在崇文院成立,中国历史上最恢弘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当时暂名《通志》)从私修(前八卷)变成了官修,司马光编修,青年历史学家刘恕、刘攽同编修,后范祖禹、司马康加入。
1067年,在位不足四年、年仅35岁的宋英宗驾崩,太子颍王赵顼继位,是为神宗。
随着神宗的继位,北宋的另一重要人物也即将出场,他就是司马光的老朋友王安石。司马光也许未曾想到,从此,与王安石唱对台戏会成为他的全部余生。
⑪
上文讲过,司马光和王安石同在台阁担任要职,但与司马光混得风生水起不同,“怪咖”王安石则不入仁宗法眼,郁郁不得志,再加上谏官的弹劾,王安石乃自请外放常州。
而神宗的继位,给了王安石机会,也彻底改变了王安石的一生。
神宗继位时,国家财政已到了崩溃的边缘,“百年之积,惟存空薄”,账薄上没钱了。没钱到什么程度?
别的不说,只说英宗的陵寝,建到一半时,居然因缺少50万资金而无法封顶,这么大的帝国竟然连50万都拿不出来了,你说这尴不尴尬丢不丢人?来来来,探花郎借你50万,哈哈。
年仅20岁的神宗想混也混不下去了,更何况他血气方刚素有大志,“有气性,好改作。”他下决心打破“祖宗之法”,改革朝政,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势,以期实现自己富国强兵目的,可谁才是自己的最佳cp呢?
大宋承平百年,文恬武嬉歌舞升平,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神宗放眼望去,满朝文武暮气沉沉,富弼、韩琦、文彦博等元老重臣都不支持变法。
神宗盘来盘去,手指头都要掰肿了,最后锁定司马光和王安石为自己变法人选,因为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都支持变法。
司马光、王安石两人虽然都支持变法,但二人对变法的总体设想、特别是在如何理财上,可以说观点是截然相反,一个主张节流,一个主张开源。
司马光是要保持现有体制不要变,现有制度不必改,只要干部用对了,何愁财利不丰,“在于择人,不在立法。”而王安石则强调要进行制度改革,从根子上解决,“变风俗,立法度。”
经过反复权衡比较,神宗最终选择了王安石主政变法。这对史上最佳君臣给合,冲突重重阻力,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史称“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
而司马光已从最初的支持变法,成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旗手人物,一场变法与反变法的大战已拉开了帷幕。
⑫
在神宗的支持下,青苗法、水利法、免役法、置将法、保甲法和市易法等在全国全面铺开。
青苗法取得初步成效,为国家创造了可观的财富;省兵置将、保甲联防既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又维护了地方治安。有了钱,军队也能打仗了,对西夏用兵也是水到渠成。
河湟大捷,一举收复河洮岷宕亹等五州,拓地二千余里,这是宋建国以来取得的最辉煌、最伟大的军事胜利,可以说是变法取得的最具体成果之一。
变法如火如荼地进行,而保守派也没闲着。随着变法的持续深入,变法不断地触动了官僚和地主合为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益,他们制造事端、展开反扑,颇有声望的司马光则成保守派反对变法的大旗。
在宋代高官中,司马光无疑是生活简朴的典范,“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对利益好像不太敏感,可他为什么要执着地反对变法呢?
这当然和他的政治观和学术观有关——“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高下、贵贱、富贫,这些都是礼之所分,分之所名,天经地义。
一句话,人的高贵贫贱都是礼规定好的,变不得,他曾说过穷人与富人“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
比如他极力反对青苗法,地主向农民放贷是合“礼”的,国家向农民放贷就是不合“礼”的,是与民争利的,国家怎么能言利呢?
司马光除了反复上书神宗反对变法外,还接连写三封《与王介甫书》,苦苦相劝王安石不要乱祖宗之法。而王安石也写了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进行回应。
如今,在王安石眼里,纯儒的司马光太“冬烘”,二人已失去对话的基础,对司马光的第三封信,王安石也不再回复,至此,二人绝交,不再有书信往来。
看到司马光和王安石二人“死掐”,老板神宗一方面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冷落司马光,为求平衡,让不同的政治派别相互牵制,神宗决定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
可司马光的牛脾气上来了,他连上六道辞呈,以各种理由拒绝枢密副使;神宗派宦官传圣旨,要司马光进宫觐见,司马光又以膝疮为由8次拒绝神宗召见。
有我没法,有法没我。司马光显然是在和神宗叫板。司马光六辞枢密副使,也让他个人声望达到了顶峰。
看看,竟然敢拒绝皇帝召见,而且是8次,司马光这是不是活腻歪了,非也,这是宋代特殊制度下的产物,宋太祖留下了“不杀言事者和读书人”的祖制,一直被严格遵守着。
所以,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气焰嚣张”,各种怼皇帝的奇葩事情层出不穷。
你不支持变法也就罢了,还不消停,天天上书反对变法,彻底成了变法的绊脚石,好吧,那就给你换个地方吧。
⑭
司马光因变法和王安石水火不容,又不接受神宗笼络,三番二次上书外调,这次神宗不再挽留。1071年,司马光判西京(洛阳)御史台,从此不再上书言事,专心编撰《资治通鉴》,这一编就是15年。
元丰七年(1084年),由神宗皇帝作序并赐名的《资治通鉴》杀青。
《资治通鉴》是编年体之巅峰,让后人高山仰止,与《史记》合称“史学双璧”。司马光与司马迁在史学界并称“两司马”,司马光也凭借《资治通鉴》进入到了中国百位历史文化名人殿堂。
《资治通鉴》最终完稿,绝不是司马光一个人的功劳,他的几个助手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请允许我再次提起他们的名字,同编修刘恕、刘攽、范祖禹,校对司马康。
在洛阳的“独乐园”,司马光过着悠闲的半退休养老生活,除了编《资治通鉴》外,就是参加富弼、文彦博组织的耆英会,后来又亲自组织真率会,组织老干部郊游、联谊等活动。
如果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会认为司马光的人生是圆满的。当然他个人不会这么认为,他觉得没能阻止王安石“乱天下”,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所以他并不甘心,他还在蛰伏、等待。
有时候,等也是一种能力,司马光等来了机会,历史没有让司马光“遗憾”,他在行将就木的时候实现了人生“圆满”。
⑮
元丰八年(1085)年仅38岁的神宗驾崩,继位的哲宗年幼,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
此前高太后一直反对变法,她主政后,保守派卷土重来。高太后先后任命司马光为副相、首相,主政台阁。
“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司马光没想到自己垂老之年还能“咸鱼翻身”,虽然此时他病魔缠身,“桃李都无日,梧桐半死身。”
就连参拜皇上、太后都不能完成(按规定四拜,高太后特批准他两拜,最后连一拜都拜不了,上班都得让人抬着。)但他一想到否定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到了,又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坚持拖着病体着手废法。
此时的司马光不知是老糊涂了还是“恨透”了王安石,只要是王安石制定的变法条例,他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废除,几乎进入到了癫狂状态,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只是新法已实施十五六年,国家财政受益良多,想一下子全部废掉,又谈何容易。
司马光的做法,不单遭到变法派的强烈反对,连保守派自己都看不下去了,苏轼等人就反对司马光全盘废除新法,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只是这时候的司马光已听不进去任何声音,他对新法的仇恨烈火愈烧愈旺,想到青苗、免役、将官三法还未动,对西夏战和之议未定,叹曰:“四害不除,吾死不瞑目!”。
保守派的范纯仁面对司马光如此倔犟,无奈叹道:又一个王介甫也!
司马光一面要和新党斗,还要和保守派内部自己人斗,实在是太难太累了,最后终于累倒了,但为了将新法全部废除,他躺在病榻上遥控指挥。
生怕看不到自己废除新法的“胜利”成果,司马光有一种时不我与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已实行十五年之久的免役法,他限定全国五日内废除。五日?没高没飞没网没电,靠跑马?这不就是瞎胡闹嘛!
本属新党的大奸臣蔡京看风使舵,立即投入旧党怀抱。时任知开封府的他为废除新法不遗余力,宣称五日内废除了免役法,因此得到了司马光的表扬。
只是司马光没想到的是,若干年后,正是他欣赏的蔡京,又亲手把他列入元佑党籍碑,昭告天下以儆效尤。
已罢相退养金陵的王安石,当他听到连保守派都认可的免役法也未能保留时,禁不住愕然失声,喃喃道“此法亦能罢乎?此法亦能罢乎?-----”不久,他带着无尽的遗憾与世长辞。
而作为军事外行的司马光,病中上书《论西夏劄子》,提出得地无用论,要将用众多将士鲜血换来的河湟地区,拱手归还给西夏。
他连篇累牍、振振有词地讲弃地,竟然连地图都没看过,更不知兰州在哪,只好叫来熟悉边防情况的官员,打开地图给他讲解给他分析。
最后在众人的强烈反对下,只好让步,不再弃熙、河、兰三州,但仍旧归还鄜延、环庆两路新取之地,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看到新法废除得差不多了,司马光长长舒了一口气,有一种完成使命的舒畅感,“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不料当他听到苏轼等人上书言青苗法、有的州县还在发放青苗款时,才发现原来“柳絮”并未消失,在西府议事的他突然昏厥,被人抬回家,从此再也没能回来。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马光卒,他是病死的,更是累死的,临死时身边还有8页未来及上奏的手稿。
司马光死后40年,北宋灭亡。有一些明、清学者甚至说,北宋实亡于司马光,虽然有点武断,但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攻倒算,并由此引发绵绵不休的党争,导致北宋国民经济凋敝,无疑加速了北宋灭亡。
如果说“书生误国”,那司马光应该算一个吧。
⑯
司马光死后,获谥“文正”,哲宗亲篆碑额曰“忠清粹德之碑”,极尽哀荣。
但同样是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又是他亲自下诏剥夺司马光的谥、告、赠典和所赠碑额。本来还有人要开棺曝尸的,哲宗未准,给他留了最后一点尊严。
此后围绕司马光的是非功过争论不休,他的名声在忠奸之间“反复横跳”,时而有人把他捧上了天,时而又有人把他踩入了地。
不可否认,司马光是世所罕见的真君子、真大儒,但为什么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又褒贬不一呢?窃以为,偏执废法是他光辉人生履历上的一大污点。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曾这样评价司马光:“温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废实,二曰防弊而启愚,三曰术疏而不逮。”
历史是有温度的,历史上的是非对错,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觉,也可以有自己的感觉,更应该有自己的感觉,正是这千千万万不同感觉,推动着人类历史滚滚向前,永不停息。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山西夏县司马光墓,历经千年战火风雨,仍顽强地伫立那里,“杏花碑”上的累累弹痕,还在诉说着墓主人的不凡过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