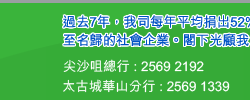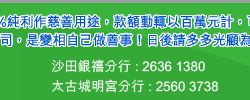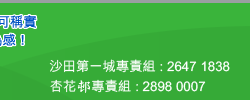1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01年。
今年,在中国是大宋咸平四年。当朝天子是宋真宗。
对于当时大宋朝堂上的人来说,今年发生的大事有两件。
一件是坏消息:八月份的时候,清远军丢了,被西夏攻占了。清远军在哪儿呢?就是今天宁夏的同心县。这件事非同小可。今天咱们没有时间展开讲,你有一个概念就行:清远军丢了,北边的灵州就变成了一座孤城,迟早也要丢。
如果灵州再丢了,整个河套地区就彻底丢了。河套,就是黄河几字型西边和上边那一段。河套一丢,不仅是领土损失的问题,是宋朝就没有养马的马场了。
在那个时代,那就相当于现代国家的坦克制造工厂没了。对于还处于对辽战争中的中原王朝来说,这个后果非常严重。

另一件事算是好消息:十月份的时候,宋军和北边的辽朝打了一仗。据说杀了辽军2万多人。如果这个数字不是虚报的,那这是宋朝15年来最大的一次对辽军事胜利。
这一段,我们今天也不展开说。因为从1000年到1004年,这五年,宋辽之间都在打仗。互有胜负。而真正的大决战,双方赌上全部国运的大决战,要等到3年后,1004年才展开,而且直接导致了澶渊之盟。
所以,这场战争,我们今天先略过,放到1004年,咱们再来展开讲。
现在,你只要有一个印象就行了。这一年,宋朝在西边,面对西夏的军事压力;在北边,面对辽朝的军事压力。而且,凛冬将至,宋辽之间大决战的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那今年,1001年,我们聊什么呢?聊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今年三月,朝廷下诏,把原先的西川路和峡西路这两个省级行政区,分拆成了益州、梓州、 利州 、夔州四个路,路是马路的路,在宋朝是一级行政区。
那么请问,为什么要分拆?
还是那句话,所有人为的历史变动,都是为了应对当事人面对的挑战。这个挑战,其实折射了当年大宋朝廷面对的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
那好,就带着这个问题,咱们一起穿越回1001年。
2
四川为什么乱了又乱?
1001年,大宋咸平四年,朝廷做了一次行政区的分拆,于是就有了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个路。

大概的位置,利州,就是今天的四川北部、陕西汉中这一带;益州,就是今天成都为中心的这一片,最小,但是最富,成都平原嘛;梓州,就是四川中部和南部这一带。夔州,中心是今天的重庆奉节,辖区就是在今天的重庆、贵州这一带。
有一个误解。很多人以为四川,顾名思义,是因为四川境内的四条河——大渡河、岷江、沱江、嘉陵江。其实不是,四川得名,就是因为公元1001年的这次行政区分拆。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因为这四个路 ,川峡四路,所以叫四川。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分拆?
如果行政区要合并,那通常是为了降低行政成本。两套班子并成一套班子嘛。背后也有一层意思,就是这个地方麻烦少,合并之后还是管得过来。
那你想,如果行政区要分拆,那正好是问题的反面啊。为什么要主动增加行政成本?大概率是因为这块地方出了大麻烦,需要加强管控啊。
那宋朝初年的四川,到底出了什么麻烦呢?
造反。不断的造反。
宋朝征服四川,就是后蜀,是宋太祖赵匡胤就干完了的事。过程异常顺利,964年十一月发兵,第二年965年正月份就搞定了,后蜀皇帝孟昶投降,总共66天。
但是,搞定了皇帝,麻烦并没有结束,当年就有后蜀降军的叛乱。总共45个州的地方,有17个州发生了叛乱,朝廷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镇压住了。
30年不到,到了宋太宗的时候,四川又乱了。993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我们在中学课本上都学过。这次起义的规模很大,人数在二十万以上,又是花了一年,才镇压下去。
这还没几年,宋真宗刚继位,997年,四川又有“刘旴(xù)之变”。就在前一年,1000年,又爆发了“王均之乱”。
这下你理解为什么朝廷要在今年把蜀中这个地方一分为四了吧?老是造反嘛。还管不了你了咋的?
那你说,这是因为四川老百姓特别爱造反吗?
当然不是。至少我们这代人的经验,就知道,四川人是有名的图安逸啊。
关于四川老百姓造反的事,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人讨论过。有人说,你们四川人爱作乱。有一个四川官员就说了,如果让家家都有五只母鸡、一头母猪,床上有简陋的被褥,蒸笼里有几升麦饭,那么即便前边有苏秦、张仪巧舌如簧的鼓动,后边有韩信、白起按剑威逼,也不能让一个人去做盗贼,更何况是作乱呢!
这段话,其实说的就是中国很多古人的心声,“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不到万不得已,谁去造反呢?四川人尤其如此。
为啥?首先是因为四川富啊,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扬一益二”,天下要比富庶,第一是扬州,第二就是成都所在的益州。富有的地方,谁不想安居乐业,谁爱去打仗?
其次,四川人的性格,确实是爱安逸。
历史上从来都是这样,只要是中原政权打过来,蜀人很少抵抗。东汉的时候,刘秀打过来,不足两年拿下;刘备入川,不足两年拿下;东晋时候桓温伐蜀,四个月;五代时候,后唐灭前蜀,七十五天;赵匡胤灭后蜀,六十六天。
后蜀的皇帝孟昶到最后就说嘛:“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遇敌,不能为吾东向发一矢。”我对你们这么好,到了用你们的时候,那真是一支箭都不肯射啊。他的宠妃花蕊夫人也有一句诗说这种情况:“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四川人不爱打仗,就到了这种程度。
当然,咱们还要补充一句,四川人并不是没有血性。蒙古攻打宋朝,四川人抵抗持续五十年。直到南宋皇帝投降后,四川仍然坚持抵抗了三年。清军入关,四川也持续抵抗十余年;更别说抗日战争时期了,抗日川军有三百多万人,死伤六十多万,那真是可歌可泣。
好了,说这么多四川人的性格,还是为了回到刚开始的那个问题:这么富庶、安逸、温厚的四川人,为什么在宋代初年叛乱不断、血流成河?
解释当然有很多种。
最明显的原因是,宋朝在征服四川之后,有滥杀无辜的行为。这是四川动乱的起始原因。
但是之所以动乱持续很多年,就得找更深的原因了,比如朝廷对四川财富的掠夺。
具体在四川上,根据曾巩的记载,就是那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他说,宋朝灭掉后蜀之后,把蜀中的财富分成“重货”和“轻货”。
重货,就是分量重价值低的东西,比如铜、布这些东西,就用船沿着长江运回开封。轻货,就是金银丝绸这些东西,就用车马运回去。
就这么水陆并用地搬,你猜花了多少年才运完?花了10多年时间。你想,那是多大一笔财富。
这是我们抽身出来,作为旁观者看到的情形。那如果你生活在当时的四川,你是个四川人,你的感受是什么?非常糟糕啊。
你会感受到:虽然搬的都是后蜀主孟昶的府库,但十来年的时间里,连车带船,我们四川的好东西眼睁睁地给运走了,那种损失感是非常直接的。要是税加得也重,还有各种各样的盘剥,那老百姓反抗,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比如,著名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的。
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一层,觉得宋代初年的四川叛乱,就是典型的官逼民反,那就低估了当时宋朝面对的复杂局面。
比起看得见的真金白银的掠夺,心理上分离主义的倾向更隐蔽,但恐怕更顽固。理解了这个问题,我们对宋代初年建国的绝大难题才能理解得更深。
宋代之前,是五代十国。我们今天理解,不都是一些分裂的小政权吗?其实你细看地图,就知道,其实五代和十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态。

我们先来看跟四川地区一拨的十国,中原周边,什么吴、南唐、吴越、楚、前蜀、后蜀、南汉、南平、闽,这些小政权,当时相对安静,而且挺有钱。为啥?
你可能想不到,这10个小国的创建者里,有9个是北方人,其中5个是河南人。为什么呢?因为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对中原地区的打击最严重,有一些军头也随着战乱从中原往外跑。因为某种缘分,他们偶然夺取了某个地方的权力,然后建立国家。
这些小国大部分有天然的地理屏障,比如前蜀和后蜀在四川盆地,周围一圈的山;南汉在梅岭以南;闽国在武夷山以东的沿海地带。
有了山川阻隔,暂时安全没有问题。因为是小国,也就没有扩张的野心。这就很容易把自己活成一个老地主,就守着一亩三分地,积极地搞生产。絮好大棉被,钻窝窝,睡觉觉。因为也不用给中央上缴,时间一长,老百姓日子过得也都还不错。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政权还比较长命,平均统治时间接近40年,最短命的前蜀也有18年。那自然就攒下了一笔比较厚的家底。有钱!
相反,五代,指的是中原政权,就是以河南为中心的几个王朝,梁唐晋汉周。它们当时位于中国的核心地带,军事实力确实超强。但是也确实穷。
为啥?因为天天打仗啊。短短五十年,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谁也不觉得这是我的万年基业,关键是要打好眼前这一仗。赢了,就还能苟着;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对境内的老百姓,当然就是能抢多少就抢多少,过了这一关再说。
周世宗不就说嘛:“我当个皇上容易吗?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搞点钱就打仗。搞来那么多钱,啥也没剩下。”
五代那样的乱世,战争之后的掠夺,更是家常便饭。正规的财政,根本满足不了需要。当时有一个词叫“括率”,括号的括,圆周率的率,这个词听起来文雅,其实内涵非常血腥,就是搜刮,朝廷临时派官员到地方去搜刮。当时有一个官职,就叫“括率使”,也是临时的,拿着朝廷的委任状,挨家挨户地强征。
所以,中原地区当然就穷。
嫌贫爱富是人的天性,让南方十国,尤其是家底丰厚的四川,心甘情愿投入中原的怀抱,其实没那么容易。
3
兵变为什么身不由己?
如果说王小波、李顺起义,还是典型的官逼民反的话,在宋朝初年,发生在四川的一场接一场的叛乱,背后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兵变。
965年的“全师雄之乱”,是兵变;997年的“刘旴之变”,是兵变;1000年的“王均之乱”,也是兵变。
兵变和民变大不相同。
唐朝后期到宋朝的兵是职业兵,称为募兵,那些人完全是靠当兵为生,比起分散的、原子化的农民,有组织的军人,更容易形成武力集团。
民变是老百姓被逼急了,反正也活不下去了,如果有人愿意出头组织,就不如赌一把。纯粹是因为经济原因。
而兵变呢?兵变,通常有三条出路。兵变要么是聚集起来闹军饷,只要钱一发,有东西吃,也就偃旗息鼓。实在不行,兵变还有一个演变的方向,就是变成土匪。
因为有组织、有武装嘛,对抗朝廷不足,欺负老百姓绰绰有余,所以就转头去抢老百姓。鲁迅不是有一句话吗,“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兵变还有第三条方向,在乱世当中,兵变闹大了,那是他们看到了干成一件大事的可能,实现一种野心的可能。
什么野心?要么是当皇帝,要么是搞割据。
那你可能会说,这宋朝都几十年了,还有当皇帝的机会吗?
当皇帝的机会可能是没有了。但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可是发生在四川,凭借山川险要,我关门落锁,搞一个割据政权,混上几十年,那还是有可能的。历史的想象空间并没有关闭。
但是问题又来了,造反毕竟是掉脑袋的买卖。我们现在说的公元1001年了,宋朝建立都40年了,中央王朝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了,为什么还有人敢做这样的事呢?
哎,这一问,就真的问到重点了。
地方割据,有时候并不简单是一个军阀野心爆发的结果,它背后往往有一套非常隐秘的动力机制,当事人往往身不由己。
要理解这个现象,就得理解一个词:“权反在下”。这个概念,出自清代历史学家赵翼,说的就是五代十国,藩镇蔑视朝廷,士兵挟制主帅的情况。
我们一般熟悉权力样式,都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军长比师长大,师长比旅长大,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好像是常识。
但是在社会的实际运行中,你还能观察到一个相反的现象,就是在某个权力位置上的人,其实也受到周围和下面的人的制约,严重的情况下,甚至是胁迫。
比如说在一个公司里,老板一定是所谓的“霸道总裁”,说一不二吗?不一定。你要是站在老板的角度想,公司里面有很多角色,他也是不敢得罪的。比如业务骨干、销售冠军、专业人士。
老板的意见如果和这些人不一致,老板没准还要委委屈屈地听他们的。所以,你看,即使是老板,他的权力也有被自下而上授权的部分。
这个现象,如果发生在武装集团里面,情况就更严重了。
你就设想这么一种情况,现在你是一个山寨的老大,手下的兄弟都服你的管,看起来权力很稳固吧?但是你心里非常清楚,兄弟们为什么服你的管?因为你能带着他们抢到金银财宝,带着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啊。
这才是你真实的权力来源,什么时候你做不到这一点了,什么时候兄弟们也就不服管了。你呢,不仅是这个位置危险,甚至性命也不保。所以,本质上,你的权力也是被自下而上授权的。这个老大也是有条件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绝对的把握,如果你有得选,你是不是真愿意做这个老大呢?
至少在晚唐、五代这样的乱世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是不愿意当老大的。我们一般对一个割据军阀的想象,都是座山雕那样的人物,心狠手辣,杀伐果决。其实在晚唐和五代时期,军阀、军头往往是被逼无奈的受气包。
我们来看一个晚唐的例子,唐德宗贞元十七年,也就是公元801年,邠(bīn)宁节度使死了。按说,朝廷应该新派一个节度使来啊。但是藩镇的士兵不干,一定要自己拥立一个。
士兵先找了一个叫刘南金的人,“你来当这个节度使。”老刘说,我不干。不干?士兵就把他杀了。再去找下一个人,找到一个叫高固的人。高固刚开始躲起来,但还是被搜出来了,“你来当这个节度使。”那刀架脖子上了。干还是不干呢?
高固说,让我干也行,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你们不能杀人;第二,你们不能抢劫。士兵说,行行行,都依你。高固就当了这个节度使,朝廷也只好正式任命他当这个节度使。
你翻开晚唐五代的历史书,到处都是这样的事,不胜枚举。有学者统计唐朝末年的藩镇动乱,80%都是以下犯上。南宋人叶适就说了,当时谁当头儿,都是下面的士卒说了算。大家一推戴,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
你看,这就是所谓“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模式。
我们处于正常社会里面,往往觉得有权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乱世,尤其是乱世的武装集团里面,把你推到那样一个位置上,是非常可怕的。造反如果失败,拥戴我的士兵可能就一哄而散,我这个头头儿肯定就活不了了。
所以,我们看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们这些人啊,贪图富贵啊,让我当天子,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啊。听我的话,我就干。不然,我就不干。”
很多人都说,赵匡胤这是假惺惺的,明明就是你自己想当皇帝,还说别人贪图富贵。但是,如果你当时站在赵匡胤身边,而且知道过去这200年的血腥的历史,你会明白,赵匡胤说的,可不是假话。
陈桥兵变真正的动力,既有赵匡胤半推半就想当皇帝的野心,也有下面将士想当开国元勋的贪欲啊。赵匡胤在披上黄袍的那一刻,心里的欲望和恐惧,说不清楚哪样更多啊。
好了,看明白这个历史背景,再来看宋朝初年四川的几次兵变,几乎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还是这套晚唐五代的剧本。
先来看965年的“全师雄之乱”。
全师雄是谁啊?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军阀吗?不是啊。
他本来是后蜀一个武人出身的官员,本来是作为降官,带着家眷要去京师的。走在路上,已经觉得不对头,乱兵起了嘛,他就怕被拥戴成叛军主帅。所以就丢弃了家人,躲了起来。但还是被搜了出来,被迫上了贼船,当了叛军的头。于是,全师雄的名字,就跟叛乱写在了一起。
还有,就是一年前,公元1000年的“王均之乱”。
这件事的起因,特别无厘头。
叛乱的军队是哪里的军队?不是原来四川当地的军队,而是朝廷的最精锐的禁军。叛乱的首发阵容有多大?八个人。领头的是什么人?一个小兵,叫赵延顺。
为什么叛乱?因为军队搞检阅仪式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这支部队,待遇不如别人好,吃的,穿的,不如人家好。就为争一口气,没有什么预谋,就造反。
那问题是,不是叫“王均之乱”吗?这个王均是谁?又是怎么上的贼船呢?
王均就是他们这支军队原来的头儿。
这事发生在1000年的大年初一。八个小兵因为一口好吃的没吃上,就开始杀人造反。刚开始可能只是因为上头了,但是真杀了人,闯了祸,这几个小兵也傻眼,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于是就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就是谁来平叛,他们就上去说,要不你领着我们造反吧?不答应?不答应就杀了。
这一连杀了好几个人。最后他们部队的主管军官,就是王均来了。他们又上去说,要不你领着我们造反吧?这王均一看,本来这就是自己的兵,闯下这么大的祸,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再说了,如果不答应,前面又有几个前车之鉴,尸体就躺在那儿呢,于是心一横,就干了。
十个月之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场叛乱才被平定。
整个这个过程,简直就是五代乱世的那些故事的翻版。同样的“权反在下”,同样的“阴谋拥戴”,领头人也是,同样的万般无奈,同样的半推半就,同样的骑虎难下,同样的鱼死网破。
这场“王均之乱”唯一的特殊性就在于,这事不是发生在晚唐、五代、宋初,而是发生在大宋建国已经40年的宋真宗时代。这说明什么?
说明此前那个乱世带来的社会结构、行为逻辑还没有被彻底消除。一个军头啸聚起来,能成事,至少能割据一方,这个历史的想象空间,至少在公元1000年前后,还没有彻底关闭。在事到临头的时候,他们还是觉得有机会。
马克思有一句话:人们是在“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宋朝建国,是在五代十国的历史条件之上创造自己的历史。宋朝建国40多年了,前代军阀的故事和传统,还是像梦魇一样纠缠着很多活人的头脑啊。
为什么统一秩序的建设这么难呢?一会儿,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4
“瓦解”为什么比“土崩”更难重建?
刚才我们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建立一个统一秩序这么难?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可能会觉得,还行吧?没那么难吧?你想,汉朝的刘邦公元前209年起兵,到了公元前202年统一全国,一共是7年时间。唐朝也是,李渊从公元617年起兵,公元624年基本统一,也是7年时间。没觉得有多难啊。
而到了宋朝,960年建国,979年拿下北汉,基本统一,这是花了19年。而直到今年,1001年,地方分离主义倾向还这么严重。40年了,还没把活儿干利索。宋朝怎么这么弱呢?
咱们不能单看这几个数字,还得看做事情的基础。那你就会发现,宋朝确实面对的是一款“地狱难度”的游戏。
有一个词,叫“土崩瓦解”。这是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发明的。这个词儿现在我们都是连着用,感觉“土崩”和“瓦解”是一个意思,都是形容一个庞然大物的解体状态。
但后来,有人就把这个词拆了,“土崩”和“瓦解”不是一个意思,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秩序溃散的状态。
什么是“土崩”?就是社会秩序彻底解体。就像一堵土墙,日晒雨淋到最后,只要有个手指头一捅,轰隆一声就全倒了,碎成渣渣,这叫“土崩”。一个社会到了这种地步,老百姓也好,精英阶层也好,都受不了。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最糟糕的秩序也好过没有秩序。”所以这个时候人心所向,就是希望赶紧打出一个新统治者,搞出一个新秩序。对,秦朝末年的刘邦,元朝末年的朱元璋,面对的就是这种局面。
刘邦和朱元璋都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都能成事。可见旧秩序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溃散状态,他们建立新秩序的难度就相对小。
但是“瓦解”就不一样了。原来的统一秩序,像瓦片一样,碎成了一块一块的。但你要是细看每一片瓦的内部,会发现仍然是秩序井然。原来的财富分布、权力结构、精英阶层都还在,甚至内部的向心力还很强。
晋朝和唐朝崩溃之后,分别留下了两个大分裂时代,就是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就是这个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要把它们整合起来,那难度就大得多了。
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土崩,就像面对一堆沙子,掺上水泥就能凝固成一个整体;瓦解,就像是面对一个打碎了的瓷碗,要把碎片粘起来,要牢固,还要不留痕迹,那就太难了。
对,宋朝的皇帝们,要想建立一个统一秩序,就是要把五代十国的碎瓷片,而且是从唐朝末年算起,已经打碎了200多年的这堆碎瓷片拼起来,难度可想而知。
其实,我们把视野放大来看这个问题,不仅是宋朝的赵家天子,也不仅是中国,对整个世界来说,这也是一个超级大难题。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包刚升老师有一本书,叫《抵达》,讲的是人类政治秩序的演化。里面开篇就开了一个脑洞。
请问,文明社会的第一块基石是什么?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肯定是私有制啊。你想嘛,一个古人把一块地圈起来,宣告这是我的。然后周边的人就信,就真的承认这是他的。这是一个奇迹啊。这就是文明社会的奠基者。
但是包刚升老师说,不对。“实际上,谁第一个对众人说‘我要统治你们,你们应当服从我,我是你们的王’,而且找到了一些居然服从了他的人,谁才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
哎,对啊,一个婴儿都可以说,这块饼干,这个玩具是我的。只要别人不抢,或者抢不过,那就是承认了他的私有权,这个好像没有那么难。
但是,一个人,一个我甚至都不认识的人,突然说,他是我的王,我的皇帝,他说什么我就得服从什么,甚至他都不用说,他制定一些法律规则,我就得遵守。你不觉得,这才是一件更奇妙的事情吗?能做到这一点,才是人类文明的一次惊险的跃进啊。
带着这个视角,我们再回到1001年的大宋,就能体察,在那么大的疆域内,在经历了200年的“瓦解”之后,还要想重建一套新秩序,确实不容易。
你就想当年的四川人嘛,我们熟悉的皇帝被你抓走了,我们的精兵被你调走了,我们的钱你说拿走多少就拿走多少,你是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姓赵的年轻人,凭啥?
你发现没有,这个问题,只靠武力是回答不了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漫长的时间,艰难的秩序建设,和一代人又一代人的逐步推进。那真是“日拱一卒”、“久久为功”啊。
就拿五代十国这短短的53年来说,听起来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笔烂账。但是如果你沉到历史的细节里,仍然可以看到中央的威权其实是一点点地在进步的。
晚唐的时候,中央搞不定藩镇,甚至皇帝都被撵得到处跑。
到后梁朱温的时候,虽然全国还是搞不定,但是他还是彻底解决了河南地区的藩镇问题,最起码,整个五代时期,河南地区藩镇叛乱,一次都没有成功。
到了后唐,又建立了一套侍卫亲军制度,就是皇帝的“私人军队”。到后汉的时候,中国北部地区的藩镇都被大大削弱了,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挑战中央的权威。
所以你看,到五代的后期,能造反成功的,就不再是地方军阀了,而是禁军的统领,后周的郭威,宋朝的赵匡胤,都是原来皇帝身边的人。
从秩序演化的角度,你能感觉到吧?虽然还是乱世,但是那个“进步”,确实在一点一点地、坚定地发生着。
文明进程就是这样,即使方向明确,人心所向,但是也急不得,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火到猪头烂,功到自然成。
公元1001年,随着四川王均之乱的平定,折磨中国200多年的地方分离主义倾向基本结束了。自此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期的、大规模的地方割据。
在这个基础上,怎么建设更好的文明和秩序,就变成了下一个挑战。

公元1001年,这一年,柳永17岁,范仲淹12岁,晏殊10岁,包拯2岁,而欧阳修将在6年后出生。历史滚滚向前,下一代人已经快要走上舞台了。
下一周,咱们1002年见。